


拨开“商”的层层光环,温州的“文”也光彩夺目。
山水诗的发祥地和戏曲的故乡就是两张极具分量的历史名片。而近百年来,在中国文坛闪亮登场的温州人同样可观。新世纪以来,作为一个松散但互有联系的群体,以王手、程绍国、马叙、东君以及先后从温州走出去的张翎、陈河、吴玄、钟求是、哲贵等为代表的温籍作家的创作渐成喷薄之势。他们的作品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国内著名刊物上频频发表、屡屡获奖,引起海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独特的文学的“温州现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容忽视的存在。
何为文学的“温州现象”?我们该如何去读懂“温州文学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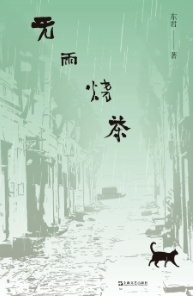
一
2006年,《江南》杂志第六期以整本杂志的篇幅,出版了一期“温州文学现象专号”,推出一批温州作家的作品,让温州文学以整体亮相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从而引发读者对“温州文学现象”的关注。
2007年,“温州文学现象”研讨会上,南帆、李敬泽、贺绍俊等国内一批知名文学批评家齐聚温州,把脉温州文学创作。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在北京举行温州作家群研讨会,聚焦王手、哲贵、程绍国、马叙、东君等五人的创作,文学的“温州现象”正式被提出。
2016 年,复旦大学举办“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研讨会,邀请张翎、陈河、钟求是、吴玄、马叙、王手、程绍国、哲贵、东君等九位温籍作家,从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跨文化角度探讨温州当代文学的独特气韵。

诚如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所言,在我们温州,在改革开放的独特道路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上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同时,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仅就文学这一块来说,温州也涌现出一批非常活跃、很有成就的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的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这个也可以视为文学中的“温州现象”。
二
毋庸置疑,温州的文学现象一开始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与温州的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不无关系。
在2010 年北京举办的文学的“温州现象”专题研讨会上,除了对温州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之外,批评家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温州现象’与温州经济的关系”,议题的背后指向的则是商业发达造成对物质的高度追求是否必然造成对精神创造忽视的疑问。而以群体性出现的温州作家似乎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厚实的经济基础恰恰能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与诸多将文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作家不同,温州的这一批作家更重视自我声音的表达。在“全民经商”氛围中,温州作家或全职下海,或投资,或家庭另有营生。经济上的宽裕,使他们的写作不再为“稻粱谋”,更多的是为了精神的满足和情感的表达。这种更加纯粹的文学创作主体姿态,使得他们关注自我个性的表达,从而逐渐形成个人化的风格。

当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则是温州文学题材的典型性。19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商业文明和伦理正在悄然地改换,跨国性的流动背后则是文化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内与外、古与今交错的现象。温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俨然成为现代中国的缩影。
生长在温州的当代作家,有一个有别于其他区域作家的独特经验世界——有关温州(人)的世界。在作家王安忆看来,地理的不方便恰是温州文学独特的原因之一:“他们在自己的‘山缝’里生长,自成一体,语言也在自我封闭中成熟,温州作家的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也就有了不同。”温州经济迅速崛起,无疑给这片热土的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绝佳素材,促成温州作家笔下别样的地方性书写。
在王手笔下,市井平民的草根生活成为其书写的重心,他的小说题材涉及“工厂、生意、江湖、社会、生死、情爱”。钟求是则以委婉细腻的笔触着力挖掘和描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人性隐秘的部分。吴玄聚焦普通人的生存哲学,而马叙的小说也不乏对小人物平庸生活的书写。
作为以商名世的温州,温州作家自然对商人和商业文明情有独钟。如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关注一群富起来的商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商场中的人情物理。相比哲贵和王手小说对商人的理解,钟求是则对商业带来的“异化”抱有警惕。
相比诸多温州作家关注温州当下的生活,东君的写作别具特色。在他带有现代先锋书写人与人之间的荒诞的作品之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借鉴古典笔记体的形式,以冲淡的笔调发掘了一个“古典乡野”温州。
温州作家的写作植根于温州地方风土,正如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教授指出的,“温州作家属于游离于文学主潮之外却能自由生长的一个群体,摇曳多姿的温州民间生活及其背后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丰富了作家们的写作元素,他们以各自的人生体验和写作形式与之对接。”这也形成了温州民间书写的多样性。
三
作为开放的城市,温州外向流动的基因也在温州作家身上展现,不少温州作家远走他乡,如移居加拿大的张翎和陈河,定居杭州的钟求是、吴玄和哲贵,出走让作家不得不面对故乡故土以外的世界,与之交汇或交锋。
当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错互动”成为常态,所以,在张翎的小说创作中,温州记忆固然成为她创作的重要资源,但并不乏与异域的互动。另一位移居加拿大的作家陈河也自觉创作了诸多与温州背景相关的小说,当然,相比书写海外移民的故事,陈河对国际性的题材书写更为倾心。
揆诸文学史,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高密东北乡”赢得了无上的荣光,也为“乡土的就是世界的”文学补充了一个鲜活的例证。以此返观当今的温州文学,我们会发现从“乡土的”走向“世界的”除了需要时间之外,还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富的想象和更深邃的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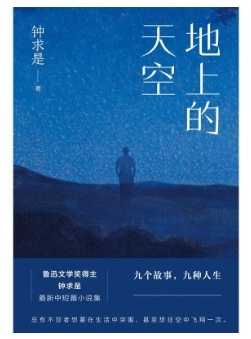
温籍作家这种更加厚重和开阔的创作形态正在不断生长。在张翎的长篇小说《劳燕》中,寓言式地表达了“温州乃至中国”在世界文化影响下的倔强生长。陈河的《误入孤城》则聚焦现代温州的“前史”。他神游百年前的偏僻孤城,以类“地方志”的形式为“温州”做传,在联通世界的视野中呈现了一个草根义气、商业流动和包容开放的“W城”。同样,走出温州的钟求是近年来的创作在坚持其对边缘生活关注的同时,对时代的思考变得阔大和深邃。
正是异乡、国与故土之间的游走,使得温籍作家从被“商名”遮蔽的角落里走向外部世界,以更开放的心态、更深度的思考和更细腻的情感书写“温州”或“中国”。
从某种意义来看,作为“地方”的温州文学书写亦是“现代中国”的书写,由“地方”而“世界”,不断生长的“文学的温州”亦表征了全球化时代“文学中国”书写的可能性。
来源:温州大学